恰好Sir这几天沐浴在广州的回南天中,脑袋反复浮现一段台词:电影叫《洛丽塔》,或者说《一树梨花压海棠》,一个“形象”的名字。世纪初,刚接触网络的“文艺青年”们应该都听说过它。原著1955年出版,讲述了中年男子汉伯特与少女洛丽塔的故事。美国,它被多家杂志和出版社拒绝,理由是,这是一本“黄书”。甚至就连作者纳博科夫本人,都多次以“这是一个肮脏的精灵”为由,欲烧掉书稿(被他的妻子从火炉前抢救出来)。电影天才库布里克改编过这部电影,那是1962年。结果女主角晚年说:“我的人生被《洛丽塔》毁了。”
花园的洒水器淋湿少女的裙子,显现出玲珑有致的曲线,她光着脚,脚趾不时蜷曲扭动。与库布里克的版本不同,1997年的《洛丽塔》对欲望毫不避讳。人们会说,青春期的少女,还不懂成年人的情爱,却渴望有人承认自己的性吸引力。花园中,看似三口之家的和睦场景,她小动作不断,汉伯特逐渐语无伦次。去夏令营前,洛奔上楼吻他后又离去,留他在原地回味。
电影给人们造成的迷惑也正在于此,人们看到一个急于展示性魅力的少女,与一个克制自己的大叔的故事。床头贴满的海报,是父亲形象的男人抱起小女孩,上面画了爱心,写着H·H(汉伯特名字的缩写)。而汉伯特,他总是对女孩露出一种类似宠爱,拿她无可奈何的神情。很多人可能不曾意识到,即便是原著小说,洛丽塔也是有“原型”的。“我对多莉所做的,或许正如当年拉塞尔,一个50岁的机械师对11岁的莎丽·霍纳所做的那样?”这个50岁的机械师和11岁的少女,便是《洛丽塔》灵感来源,1948年,大叔诱拐少女,以父女的名义,穿行各州长达21个月。而被持续诱奸的少女受害者莎丽·霍纳,因为失去贞洁,后被人们称为“荡妇”。看起来,这是一个未成年少女投怀送抱的“荡妇”故事。可片中多处,汉伯特的画外音响起,以“尊敬的陪审团”开头。车上,洛对汉伯特的搭话,根本懒得理睬。不断摆动的雨刷器,加剧着汉伯特的焦虑,也反衬出洛的冷淡。床上,她总下意识流露厌恶,得知两人要住同一张床,洛并非毫无羞耻心,她用疑问来表达抗议。可在汉伯特目光之外,他的叙述无法覆盖到的角落,女孩被关在房间里,独自哭泣。在很多女性受害者的案例中,常常被问起的一个问题是:天真者的想象中,反抗,似乎就和点餐时拒绝一样食物那么简单。《洛丽塔》的故事中,同样地,在汉伯特极具欺骗性的深情中,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关系是天然的不对等。起初,汉伯特能用糖果和旅行,来吸引小女孩,可一旦对方表现出反抗,他便企图操控她的日常生活。再到她零用钱,交际对象,甚至是她的身体(和谁发生关系)……都要干涉。我们看到他对洛的痴情和耐心,看到他因爱卑微,被爱折磨。一个14岁的少女,失去唯一的亲人母亲之后,她用什么反抗。但当一次又一次地用性来取得报酬时,性就成了工具——她能够勉强可以与汉伯特“讨价还价”的工具。换言之,汉伯特从来没有把洛丽塔当作一个有独立思想的“人”来看。他爱的,是他“想象中”的洛丽塔,无关她的个人意志。令我着魔的不是她,而是我自己创造、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,也许比洛丽塔更真实……没有意志、知觉,缺乏真正的生命。
你可以说是无意,但当“狗”这一意象在电影中出现4次,便值得被关注。
汉伯特初到美国小城,车外小土狗不停狂吠,试图引起他的注意。下了车,他遇到同样试图吸引他注意的洛。旅途中两人办理入住手续,洛逗弄作家奎尔迪养的贵宾犬。这是一只宠物狗,仔细看脖子上拴着绳索。一只恶犬突然冲出来,冲他咆哮,它愤怒,攻击性强,是别人家的看门狗(此时洛已经爱上了奎尔迪)。在她家门前,有一只看起来有品种、却蓬头垢面的狗,性格温顺,对陌生人也挺友好。
形容憔悴,怀有身孕,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,过上了普通平静的生活……而对于被套上绳索的洛来说,她又有多少的选择空间呢?人们沉溺于自己偏执的观点中,无法认同别人的看法——以至于导演愤恨地说,“如果我拍一个13岁女孩被食人族吃掉的故事,是没问题的。”他没有预料的是,在当下,这也是有问题的。某种程度上,它是那个年代的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,只是因为男性叙事,只是因为艺术性地不那么直白,引起不少误解。《洛丽塔》又不仅仅是控诉恋童癖那么简单,它提供的,是一个远比暴露、批判更有价值的艺术文本。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容许各种互相对立的读者层的;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一个每位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不同含义、不同特色、甚至不同故事的潘多拉的盒子。
多年来,对这本小说和这部电影的讨论,读者和观众乐于挖掘、解读它种种不易察觉的细节,和复杂的情感脉络。1955年,有出版社形容它是“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年老的欧洲”。洛丽塔早熟、艳丽、粗鲁、诱惑十足,是为美国;汉伯特优雅、博学,也有陈腐气,对故土怀有美好记忆,是为欧洲。虽然作者纳博科夫个人不认同这类有象征意味的“阅读理解”。
正如作者纳博科夫本人就说过,写书不是为了道德教育,而是美学上的追求。
我想补充的是这种美并不是它表面显现出来的一种病态的美、离奇的美。它的美在于它对人的情感中某些幽深的东西的捕捉,对人性中某些共通的东西的映射,在于它披着病态、离奇的外衣,却照见了我们自身。
文学、艺术作品的最大魅力,不在于解释道德,而在于描绘人性,描绘美。文学或电影的最大意义,在于照见现实中的我们自身,然而怪的是,很多人却颠倒了此种顺序:一个本不是恋童癖的人,大概率不会因为看了《洛丽塔》就变成恋童癖。但一个确实是恋童癖的人,我们绝不能用《洛丽塔》来为其开脱。阅读和观看罪恶不是为了去理解、去合理化它,也可以是为了在现实中警惕它。
就像作品中纳博科夫终其一生追求的那只蝴蝶,象征着自由与美的蝴蝶。

关注公众号:拾黑(shiheibook)了解更多
[提示]友情链接:
法律法规检索大数据平台:https://www.itanlian.com/
盘点娱乐资讯黑料不打烊:https://www.ijiandao.cn/
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:https://www.0xu.cn/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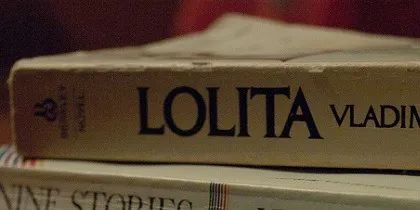



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
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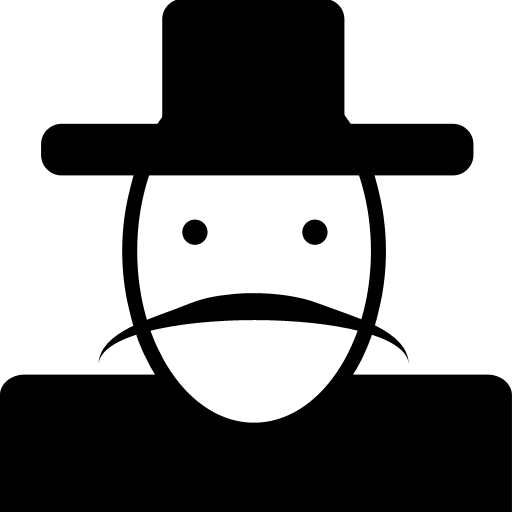 Sir电影
Sir电影






